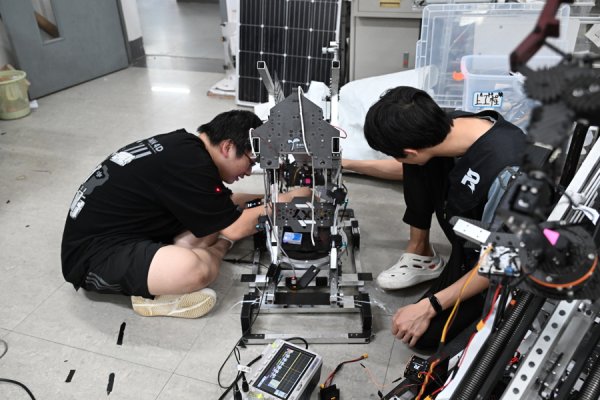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回顾与展望在线股票配资门户网
曹中俊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摘要:丝绸之路青海道是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支线,学界相关研究已走过八十余年的历程。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道路相关史事、遗物遗迹的个案研究,未能将相关内容置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进行综合梳理,大多显得各行其是、缺乏融通。因此有必要对相关研究成果做简要梳理和评述,内容主要包括丝绸之路青海道概念及内涵研究、路网构成探索与研究、沿线考古发现及研究、青海道上相关族群研究等。当前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面世与族群理论的引入,青海道的内涵与价值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变迁等问题亟需重新思考与审视。在此后的研究中需要充分把握青海道“三位一体”的特性、开辟族群与道路结合研究的新思路以及将文化变迁考察与道路变迁研究有机融合,推动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丝绸之路青海道作为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支线,对于认识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对于青海道的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从对青海道概念基本认识的形成,再到如今对青海道沿途地区的综合考察,相关研究不胜枚举,但目前来看,有关青海道的整体性观察依然较少,一方面,路线研究具有“资料梳理多,学理阐释少”的特点,另一方面,相关考古发现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对于这些发现的研究也多以微观性视角为主。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面世与族群理论的引入,青海道的内涵与价值,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变迁等问题亟需重新思考与审视,因此有必要先对相关研究成果的特点进行总结与评述,再针对具体问题对青海道研究提出几点思考和希冀。以下,对相关研究择其要者,分类进行综述。
展开剩余97%一、丝绸之路青海道概念及内涵研究
当前学术界关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概念有很多种,如羌中道[1]、羌氐道[2];吐谷浑道[3]、吐谷浑路[4];河南道[5];青海道[6]、青海路[7]等。此外,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部分通道曾是玉石、彩陶、小麦以及青铜等传播的重要通道之一,因此,有学者常以“玉石之路”[8]、“彩陶之路”[9]、“青铜之路”[10]命名此通道,本文所讨论的丝绸之路青海道概念,即基本是在汉唐丝绸之路时间框架下所展开的,但是在道路走向和内涵阐释等方面,学界的分歧较为明显。
例如,近年来,一些学者虽然已经意识到目前“学界有关丝绸之路青海道命名与构成的描述或者与历史事实不符,或者缺乏典型性,需重新梳理”[11],但直接将青海道分为羌中道、河南道和湟中道三条干线的做法,似乎欠妥。
总体来看,虽然不同学者以不同时期、不同族群为出发点提出了若干种有关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命名方案,但是对于主干道走向和青海道的内涵则已基本达成共识。具体而言,从青海道途经区域和内涵的差异来看,其概念应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丝绸之路青海道是指由高昌走焉耆,去鄯善,越阿尔金山口,穿青藏高原的白兰地区,至察汗孙河的都兰城(河南国都),经柴达木盆地,抵吐谷浑东镜龙固(松潘),南入益州(成都),再由益州达建康(南京)的交通道路。狭义丝绸之路青海道主要是指在今天青海境内的交通路线,主要包括从西宁直接北上穿祁连山扁都口至张掖,亦可从西宁、共和等地出发抵伏俟城或都兰,而后沿柴达木盆地南北缘行走,南缘穿越阿尔金山至若羌,北缘跨过当金山口达阳关、敦煌,可贯通青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常常将青海道与河南道混为一谈,徐苹芳在1990年前后就已将青海道与河南道做过区分[12]。狭义的河南道是指由青海、甘肃南下进入以益州为核心的蜀地路段。而广义的河南道一般是指由东晋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出发,沿长江水路溯江而上到达蜀地益州(今成都),经岷江或白龙江北上至甘南迭部、临夏,后经民和、同仁等地达西宁,后与青海道相衔接。在整个路线中建康至益州的长江水路,是由建康至益州、河西及西域的必经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段长江水路是丝绸之路河南道沟通中西的重要辅路。
整体来看,丝绸之路青海道是对青海境内丝路交通的一个总括,而不单指某个时代、某个民族绾毂的交通路线,用青海道来囊括整个路网较为合适、恰当,不易混淆,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二、丝绸之路青海道路网构成探索与研究
弄清丝绸之路青海道的走向、探索丝绸之路青海道的路线一直是从事青海道相关研究的学者们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学者们最早从地望入手,主要依据的是文献材料,后来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增多,为青海道路网的研究和路线复原带来了新的契机。
如1948年,吴景敖首次从地理学角度将西域、青海、成都、建康诸地联系起来考虑。他指出,由隆务河流域向西,原有三条通道可以通往青海西部;由隆务河向南经行洮叠二州可以通往南朝[13]。之后,吴景敖又发表几篇文章来讨论南北朝时期西域与江南之间存在的交通通道。他认为:该道由汉中地区出发,途经昭化、洮州、叠州、柴达木盆地南北两沿以及当金山口,可以抵达西域[14]。在吴氏的基础上,严耕望继续讨论了川甘青地区间的交通路线,如《唐代交通图考》不但考证了青海道的交通路线,还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海道是重要的军事交通线。此外,在第二卷《河陇碛西区》十三篇“河湟青海地区军镇交通网”中论述的“临州西通鄯州河源军道”“鄯城河源军之辐射交通线”及“赤岭西南青海河源道”也与丝绸之路青海道有关;而第三卷《秦岭仇池区》十九篇“汉唐褒斜驿道”中提及的“汉魏褒斜古道”即为“青海道”的褒斜道[15]。
1958年,夏鼐根据对古代文献记载的研究,认为从中原出发,途经吐谷浑所居地去往西域的道路主要有三条[16]。徐苹芳在夏鼐的基础上,进一步勾勒出了三条路线的走向。他认为,青海道从(丝绸之路)南路之兰州或北路之靖远返兰州,西经乐都(鄯州)、西宁(鄯城),北走大通,过大雪山扁都口(大斗拔谷)至张掖;或自西宁过日月山(赤岭),沿青海湖南岸至伏俟城(吐谷浑国都);或自西宁至海晏三角城(汉西海郡故城),沿青海湖北岸和柴达木盆地北缘至大柴旦,北上穿当金山口而至敦煌;或从伏俟城沿柴达木盆地南缘,经都兰、格尔木,西出阿尔金山(茫崖镇)至若羌[17]。1982年,周伟洲梳理了青海道的大致路线[18]。1985年,赵荣结合青藏的自然地理及相关文献资料,对青海道的走向及路线进行了有益探讨[19]。1988年,薄小莹根据文献考证出从益州到西域的青海道分为北线、南线东段和南线西段[20]。另外,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前田正名、佐藤长、山口瑞凤、铃木隆一和阿子岛功等在其论著中都有讨论过青海道[21],其中佐藤长深入研究过青海道的交通路线[22],认为“游牧民的根据地自古未变,路线一旦确定,沿线诸民族的位置也随之显现,情况更加明了”[23]。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两次组成工作队前往青海道沿线进行实地考察,行程约15000余公里。1992年9月至10月,主要前往四川成都、郫县、灌县、汶川、彭县、绵阳等县进行考古调查。1993年1月至10月,主要前往四川茂汶、松潘、南坪,甘肃岷县、迭部、合作等县,青海共和、贵德、贵南、都兰等县进行考古调査[24]。之后,陈良伟又多次前往青海道沿线的若干支道进行调研,收获颇丰[25]。
2002年,陈良伟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丝绸之路河南道》一书,此书是20世纪90年代起,陈良伟等人对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实地调研的重要成果。书中不仅对前一阶段学人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同时还开创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的新思路,极大地推动了青海道的研究进程。徐苹芳评价这本书“是目前所见文献学和考古学两方面资料最全的论著”[26]。综合调研的成果,陈良伟将青海道分成四条分道,分别为西蜀分道、河南分道、柴达木分道和祁连山分道。四个分道又可细分为九条支道,即“岷江支道、白龙江支道、河源支道、隆务河支道、洮河支道、柴达木南支道、柴达木北支道、扁都口支道和走廊南山支道”[27]。这些分道和支道常常需要互相串行,互为辅线才能支撑河南道的畅通[28]。关于陈良伟对青海道路网的划分,李健胜等认为其对部分路线的表述值得商榷,且对湟中道干线及其支线网络的研究也不够深入[29]。
2013年,仝涛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英国出版了《中古早期青藏高原北部的丝绸之路:依据考古与文献资料的重建》一书。该书利用考古出土材料及传世文献资料较系统地对青藏高原北部地区的丝绸之路路网进行了梳理,并对沿途文化交流等现象进行了有益探讨[30]。
此外,在研究青海道路线问题时,我们亦要关注历史上经行过青海道的使团、僧团、商团、军团等人群,他们行进的路线记载为复原、细化青海道路网构成提供了重要资料。以使团为例,日人松田寿男[31]和唐长孺[32]早年探讨了吐谷浑、高昌、粟特等族群经河南道与南朝交往的史实。后来周松、陈良伟、李健胜等从不同角度综合分析了经行青海道的使团情况,其中对经行路线多有涉及[33]。李智信的《青海古城考辨》对青海境内的古城进行了系统梳理,是厘清青海道交通网络的重要学术参考[34]。毕艳君、崔永红合著《古道驿传》一书,较系统地梳理了青海境内的古道、驿站,亦是研究青海道交通网络的重要学术基础[35]。
近来,综合各家的研究成果,周伟洲[36]、张得祖[37]、苏海洋[38]、崔永红[39]、李健胜[40]等学者结合史料及考古发现又进一步研究了青海道的路线,不仅加深了我们对青海道几大干道内部支线情况的认识,还让我们意识到几大干道之间可勾连、交并,且青海道亦可与其他丝道相连通,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沟通东西的庞大路网。
三、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考古发现及研究
(一)近年青海道沿线考古发现
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研究进程最早由外国探险家们开启。瑞典学者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年)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四次前往青海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研究工作,并发表了《亚洲腹地旅行记》(My Life as an Explorer)等论作[41]。20世纪30年代,德国冒险家威廉·菲尔希纳(Wilhelm Filchner)在都兰及周边地区实地考察、调研[42],这些工作为后来青海道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建国以后,尤其近20年来,伴随国内考古工作的逐步展开,在青海道沿线发现了诸多相关遗存。
1.城址
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分布古城众多。1943年,靳玄生在《青海历代城垒遗地考》中指出,青海湖西约7.5公里的铁卜加古城当为南北朝时期吐谷浑王国的国都伏俟城。
1958年,安志敏对海晏县三角城进行了考察,并确定它就是王莽时建立的西海郡城[43]。1980年以来,随着青海文物普查工作的全面开展,文物考古工作者们调查、登记了大量古城遗迹,确定出大量的古城建造年代,研究得出一些古城的原名。李智信的《青海古城考辨》即对青海境内的古城进行了系统梳理,为研究青海古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对丝绸之路河南道沿线调研的重要古城进行了梳理和公布[44]。这是第一次科学地、大范围地、有计划地对青海道沿线古城进行实地调研,最重要的收获便是发现了数十座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能够反映西南地区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面貌的城塞。其中绝大部分城址年代为南北朝时期至唐代前后,这对于弄清河南道沿途所经有着重要意义。此外,青海考古工作者还对天峻县的加木格尔滩古城进行了试掘[45]。
2.墓葬及出土文物
青海河湟地区人口稠密、城镇众多,因此墓葬分布也较多。与丝绸之路青海道关系密切的墓葬主要有中华巷汉墓群、南滩汉墓群、彭家寨、刘家寨汉墓群、上孙家寨汉晋墓、多巴汉墓群、高寨汉晋墓群、南凉康王墓等[46]。这些墓葬出土有各式陶器、木器、骨器、漆器、铜器和五铢钱等,还发现刻有“彭安世”“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等字的铜印,以及汉晋墓葬胡人牵驼画像砖、带有西方帕提亚色彩的银壶等文物,引起了学者们的重点关注。
环柴达木盆地及邻近的青海湖地区是历史上吐谷浑人活动的重要区域,自20世纪80年代起,该区域发现诸多墓葬,主要集中在海西地区的都兰、乌兰等地。如以热水一号大墓为主的墓群、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乌兰泉沟一号壁画墓、哇沿水库墓葬群、香日德古墓群、芦丝沟龙根墓地、智尕日墓地、郭里木墓地、白水河河口西岸墓葬、贡艾里沟阿门墓葬、艾力斯太墓葬、哈日吾足尔墓葬、额日德尼奥木仁墓葬等[47]。这些墓葬出土文物主要有骨器、漆器、木器、铜器、古藏文简牍、彩绘棺板画及各式装饰品。且这些墓葬中还发现众多与西方文化联系密切的精美丝织品、金银器、钱币及装饰品等[48]。
3.窖藏发现及石窟寺等佛教遗迹
1956年,工人们在西宁市内隍庙街(今解放路)施工过程中,发现窖藏于地下的陶罐一件,里面除盛放有100余枚萨珊银币外,还有货泉、开元通宝等近20枚铜币。这些萨珊银币直径2.5至3厘米,重3.8至4.1克,平均为3.95克,是研究东西商贸及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49]。
青海道沿线现存一些重要石窟,如丹斗寺岩窟、红崖石窟、炳灵寺石窟等,在青海湟中地区出土有佛教题材画像砖,青海玉树和昌都等地发现有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在青海道河南分道沿线,如岷江上游[50]、成都万佛寺[51]、成都商业街[52]、成都西安路[53]及成都下同仁路[54]等地还发现了诸多佛教造像。这些实物资料为我们研究佛教在地化进程等问题提供了切入点。
(二)针对考古发现的相关研究
1.青海道沿线城址研究
利用考古学方法,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青海古城进行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即上文提及的1958年安志敏对海晏县三角城所做研究。
吐谷浑在青藏高原上立国长达350余年,其中晚期时的都城——伏俟城的发现引起了学者们的热切关注。1960年,黄盛璋和方永结合亲身考察经历,例证其发现的古城即为吐谷浑伏俟城,并阐述了伏俟城发现的意义及伏俟城在当时的交通地位等[55]。1995年,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结合考古工作人员新调查所获资料,对青海相关古城涉及到的地名、城名、道路名、桥名等进行辨析,其中讨论的部分城址在青海道沿线上。
近来,2018年和2020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前往伏俟城进行勘探和发掘,厘清了内城城内建筑布局,发现并确定了外城北墙和城门,在外城南部发现房址和灰坑。通过考古钻探和遗物测年,联合考古队进一步确定了青海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城就是吐谷浑伏俟城,印证和补充了历史文献的记载[56]。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洛阳伽蓝记》中所记宋云一行经过的“吐谷浑城”应是位于今天青海省都兰县的香日德古城[57]。
2.随葬品及葬俗研究
最早以考古学视角研究青海道的学者是夏鼐,他于1958年首次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了丝绸之路青海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58],此后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众多学者开始关注丝绸之路青海道,并对墓葬中的随葬品及葬俗进行了研究。
王瑄从封土类型、墓葬结构、随葬遗物等方面对都兰发现的墓葬群进行了分析[59]。肖永明专门撰文公布了对青海西部地区墓葬中的棺板进行树木年轮测年数据。并结合西藏地区吐蕃时期的墓葬,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等方面对青海西部地区墓葬进行了年代和族属的判断[60]。这些研究为之后进一步对青海道沿线墓葬进行分区、断代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青海道沿线民族众多,区域内的历史文化发展复杂,关于墓葬的族属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尤以都兰热水墓群的墓主人族属问题最具代表性。最先学者们围绕吐谷浑、吐蕃、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等说展开了激烈讨论[61]。以霍巍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将都兰墓群的族属定义为“吐蕃占领或统治下的吐谷浑人”较为客观、公允[62]。这一观点虽获认可,但仍有一些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不过随着2018血渭一号墓中出土了一枚刻有古藏文“外甥阿柴王”银金合金印章,此类墓葬的墓主人及族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但是我们仍要观察到墓葬之间的细微变化。因为若一批墓葬同属于7世纪的吐谷浑人,但以吐谷浑灭国的龙朔三年(663年)为界,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文化因素的外在表现形式等方面还是有些许不同的。
虽说大多都兰热水墓葬里蕴含有丰富的吐蕃因素[63],但是一些学者仍敏锐地观察到墓葬中可能存在鲜卑文化因素,如葬具大多为木质梯形棺等[64]。且在海西地区5-8世纪墓葬中汉和鲜卑文化因素仍占主导地位[65]。
3.图像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前述青海道沿线出土众多文物中包罗各式图像,这些图像吸引了较多学者对其进行讨论,涉及主题包括纹饰造型、艺术来源、渊源和流变、风格特征等。首先是出土丝织品纹样的研究。1991年,许新国、赵丰二人对都兰出土丝织品上的图案分为骨架式排列和图案式排列两大类,包括对波骨架、套环骨架、几何形骨架、簇四型骨架、环形团窠、独花团窠等纹样[66]。许新国对其中的联珠圈含绶鸟纹做了个案研究,将蜀锦、粟特锦、波斯锦等作了区分和比较[67]。另还撰文讨论了太阳神[68]、人神搏斗[69]等都兰墓葬出土蜀锦的纹样,及其传入青海的路线[70]。此外,赵丰主编的图录[71]及论著[72]中也有涉及到对都兰出土织锦纹样的阐释和分析。近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阿贝格基金会合作编著《都兰丝织品珍宝》一书,对青海出土的丝织品进行了公布,其中包含大量之前未公开的丝织品及高清照片,为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73]。
其次是金银饰片及器皿装饰图案研究。瑞士学者艾米·海勒(Amy Heller)自2003年起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分析了吐蕃金银器,其中涉及到都兰墓葬中出土金银器的图像分析[74]。国内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要数霍巍和许新国二人的研究。霍巍对出土金银器上的宝马与骑士形象、半人半身形象、带翼神兽、胡瓶等图案进行了个案分析[75]。另外《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一文,对于我们研究青海道沿线出土金银器艺术风格渊源有着重要启发和参考意义[76]。许新国则对都兰墓葬中出土的动物形银器进行了考证,推测其与粟特金银器有着密切关系[77]。另外李璟[78]、朱建军[79]等学人对青海道沿线新出金银器中蕴含的多元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
最后是棺板画呈现的画面研究。目前学界对青海道沿线出土彩绘棺板画已有较多成果,既有一些棺板画图像综合研究[80];也有一些个案研究,关注较多的有棺板画中人物族属[81]、人物服饰[82]、棺板装饰[83]及丧礼[84]等问题,还有学者以棺板画为核心,论证了粟特艺术东传青海的路线及相关问题[85]。此外,还有从统计学的角度展开研究[86],不断丰富了我们的认知。近年辛峰、马冬[87]、孙杰[88]、张建林[89]等学者也在不同文章中披露了诸多此前未见的青海木棺板画。
4.其他发现的相关研究
除了上述研究外,还有一些涉及宗教文化与艺术传播,以及与青海道途经区域相关的考古研究等,简要评述如下。
日本人岚瑞徵最早于1936年利用诸本高僧传的记载,专文梳理出了六朝时自西域经行青海前往成都和江南的佛僧,他只是提出存在这条通道,但并未对具体道路名称和路线等进行深入发覆[90]。1958年,夏鼐由西宁发现的窖藏萨珊银币而讨论这条比较稍南的交通路线时,论证了文献中的法显、昙无竭、阇那崛多、宋云等佛僧往来西域曾经行过这条道路[91]。唐长孺于1979年讨论北凉承平七年(449年)写经题记中的“吴客”及相关问题时,提到昙无竭、释法献、阇那崛多、宋云及惠生几位僧侣可能经行了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河南道”[92],这是学界首次明确指出这些佛教僧侣经行的就是历史上的青海道,这对于研究青海道上的佛教传播具有重大意义。2002年,陈良伟考证出除以上学者提到了几位僧侣外,还有单道开、昙摩密多、释法绪等20位中外僧侣也曾经行过青海道[93]。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进一步考证和推定了耆域、佛陀耶舍也可能经行过青海道及22位经行青海道的僧侣可能经行的具体路线[94]。
此外,学者们在讨论佛教入蜀时间和造像入蜀路线时,也多次涉及到青海道。1992年,吴焯认为四川早期佛教及其遗物的传播途径或者说路线,系由西北印度、中亚经西域,穿越青海道进入蜀之西界,复沿岷江向东发展[95]。日本人山名伸生认为,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是通过吐谷浑与西域各国作为渠道传来的,这条线路是由西域、吐谷浑到成都,再顺长江而下到达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96]。吉村怜对山名伸生的说法进行了反思和质疑,认为成都佛教造像有经吐谷浑渠道传入,但不占多数。大多还是南朝首都建康给成都带来了强烈影响,其中路线为以长江为主的漕运[97]。
近来,孙杰[98]和仝涛[99]以图像和考古材料进一步讨论了青海地区的佛教发展情况,间接证明了青海为佛教经西域入蜀的中间地带,印证了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学术接力,佛教僧侣、义理、造像从西域经青海、甘肃、川西入蜀的传播路径愈发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当然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建康对蜀地佛教发展的影响。
青海道沿线地区也有道教的传播和交流,王育成对都兰热水墓群中发现的道符进行了研究[100]。张泽洪通过分析认为吐谷浑宗教受丝绸之路河南道(青海道)的影响,儒释道三教与原始宗教信仰并存于吐谷浑社会[101]。
除了佛教和道教外,近年祆教东传青海道也为一些学者所关注。许新国最早关注到都兰一号大墓殉马坑里的舍利容器当属粟特系统金银器,认为可能与使用纳骨器的粟特风俗有关[102]。艾米·海勒认为这只银质珠宝箱,看上去是准备用来装sarira(一种纪念品)的,可以与粟特银质遗骨匣盒及唐朝的金银遗骨匣进行联系[103]。霍巍对此持审慎态度,并认为假若都兰此容器性质与粟特遗骨匣相同,那么我们应当重新认识青藏地区的古代宗教及其不同葬俗的流行状况了[104]。张建林等针对青海省藏医药博物院收藏的数块棺板画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编号ZB–M00001棺板画蕴含有些许中亚祆教元素,如祭司、火坛等[105]。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城址、烽燧、渡口、桥梁、驿站等资料还可参考陈良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和崔永红的《丝绸之路青海道史》。2001年,德国地理学家安德雷(A. Gruschke)在其《西藏外围青海地区的文化遗迹》一书第六章中简要介绍了都兰吐蕃墓等非佛教遗迹,为了解青海地区的文化史及相关遗迹提供了丰富的地理学信息[106]。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编的《热水考古四十年》对相关考古资料和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汇集整理,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便利[107]。霍巍的《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108]和仝涛的《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109]一书中有诸多内容涉及青藏高原的对外交通路网及出土文物,且大多都配有彩图,为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素材和研究思路。此外,赵丰主编的《西海长云:6-8世纪的丝绸之路青海道》[110]不仅包括与青海道有关的历史、艺术、墓葬及相关丝织品的高质量研究论文,还提供了青海道沿线出土文物的诸多细节描述及照片,为研究青海道的历史及吐谷浑文化带来了新的契机。
四、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相关族群研究
一条道路的存在及畅通,往往与沿线民族的经营与绾毂息息相关。就丝绸之路青海道而言,其在民族迁徙、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学者们主要围绕不同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生活的不同民族展开讨论。
早在战国初期,秦献公兵临渭首,河湟羌人为避其兵威,向黄河以南迁徙,移居到岷江、白龙江、西汉水乃至长江上游一带和氐人生活在一起。至两汉时期,青海道沿线主要区域生活的仍是羌人和氐人。穿行于古羌人聚居地,加之由羌中通西域,在《史记·大宛传》中已有“并南山,欲从羌中归”的明确记载。初师宾从汉王朝征伐羌人的角度分析了羌中道的开辟[111],吴焯结合西羌历史探索青海道的起源[112]。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青海道因吐谷浑人的绾毂,而渐至兴盛。众多学者从事吐谷浑与青海道的关系研究。唐长孺是第一个将吐谷浑部族放进丝绸之路青海道(河南道)中分析的学者。后来的学者黄文弼将丝绸之路青海道称为“吐谷浑道”,并认为此道“开于北魏时之吐谷浑人,历隋唐数百年间,未曾荒废,而与西域之文化、民族关系甚大”[113]。在其1939年11月自绘的《西域交通路线图》和后来改绘的《中西交通路线示意图》中,都明确标有吐谷浑道。周伟洲在《吐谷浑史》[114]一书中谈到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兴盛始于吐谷浑慕利延在位的后期,即公元五世纪四十年代前后。随着青海道的兴盛,吐谷浑在中西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罗新以经吐谷浑开展的玉石及玉器贸易为切入点,阐明了青海路在南北朝时发挥的重要作用[115]。李朝先后发表数篇文章来探讨吐谷浑经营下的丝绸之路青海道,他认为青海道是在穆王道、羌中道的基础上,经由吐谷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营逐步完成的[116]。他强调吐谷浑开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为中西商贸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17]。石云涛在《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一书中也直接将丝绸之路河南道称之为“吐谷浑之路”,强调了吐谷浑道在三至六世纪时期于接通西域方面极其重要[118]。许新国以都兰出土的蜀锦论证了“吐谷浑路”的重要性[119]。近年,朱悦梅与康维的《吐谷浑政权交通地理研究》重点分析了吐谷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置身于不同的地缘政治关系之中,从而交通格局始终发生着不同的变化[120]。
随着唐朝公主入藏和亲,汉藏交流增多,唐蕃古道日益兴盛,其中就有经行青海道的部分路线,尤其吐谷浑亡于吐蕃后,青海道几乎全程在吐蕃辖境之内,吐蕃继续掌控青海道,并进一步开拓青藏高原对外交流交往的多条通道,使青海道又继续兴盛了一个时期。近来有学者提出“高原丝绸之路”的概念,将青海道作为其中的一个分道纳入其中[121]。沈琛对伊斯兰史料与藏汉文史料的梳理,结合青藏高原的考古发现,再现了吐蕃与中亚的商贸往来,提供了一个窥探吐蕃经营高原丝绸之路对外交流的切入点[122]。
此外,柔然、粟特等民族,虽然没有直接生活在青海道沿线,但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与青海道有着紧密关系。唐长孺爬梳史料后发现柔然(芮芮)与南朝交往频繁,两者之间经常互通使节[123],这印证了吐鲁番所出佛经题记中的相关记载[124]。周松[125]、陈良伟[126]等学者探讨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古代政治交流情况,其中柔然的使节常常需经行青海道前往南朝。
粟特人作为中古时期横贯欧亚大陆的重要贸易者,本着“利之所在,无所不至”的原则,也来到了青海、四川等地经商,丝绸之路青海道成为他们迁徙及从事贸易的重要线路。最早关注此问题的是唐长孺,他在《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一文中讨论《何妥传》时指出,何妥家族定居在郫县一带,应是依附于本族人[127]。后来荣新江对有关入华粟特人东迁的路线考证,其中就包括粟特人经丝绸之路青海道进入到西南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128]。法国学者魏义天的《粟特商人史》中谈到四川的粟特商人可能未经甘肃通道,而是从于阗到柴达木盆地,经青海南下到达四川的[129]。林梅村翻译的一件吐鲁番粟特古文书即可看到九至十世纪时粟特人的贸易网络仍包含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部分地点[130]。许新国结合青海都兰等地出土的文物资料,对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兴盛及其在中西交通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系列研究,其中也有涉及到青海道上的粟特人[131]。霍巍通过文献与新出考古材料的分析,认为汉唐时代粟特人不仅已经活动在青藏高原,而且通过具有重要交通意义的“青海道”,与中国西南地区很早便有可能产生了商贸交往[132]。近年,李瑞哲进一步深化了对粟特人在西南活动踪迹的探讨,结合青海地区出土的木棺板画、金银器、丝织品等材料展示了青海地区的西域文化传统,并论述了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交流得益于吐谷浑道(青海道)的开辟[133]。还有相关主题文章虽涉及到青海道,但无新意,故在此不一一收录、赘述。
综上,青海道的形成、发展、畅通直至衰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生活在沿线的众多族群都为青海道的畅通和繁盛做出了历史贡献。以河南道(吐谷浑道)为中点,在其之前羌氐道、羌中道为河南道(吐谷浑道)的畅通打下了基础,在其之后的唐蕃古道、青唐道是河南道(吐谷浑道)繁荣的延续。
五、结语
回顾八十余年来学界对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研究历程,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目前学界对青海道的沿革和走向已基本廓清;对沿线所经区域和涉及民族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对沿线政治、商贸、军事、思想、文化艺术交流等方面已有较多认识。但是相关研究各有侧重,整体性观察仍显不足,尤其是受学科设置所限,有关青海道历史地理的研究与青海道途经区域的考古发现及研究严重脱节,道路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也挖掘得不够深入。种种迹象表明,丝绸之路应是一条“活”的道路[134],是动态的道路,其核心应是人,而不是路。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研究而言,动态地观察必须要将路和人作全面考察,并形成“路—区—人”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藉此,笔者不揣冒昧,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几点“思考”。
第一,研究过程中应充分把握青海道“三位一体”的特性。当前学界对青海道的研究往往只关注道路本身,对其路线、路网及直接相关问题涉及较多。那么青海道沿途所经区域和道路上的人与文化的相关问题是否能纳入到青海道的研究范畴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学术问题。即我们应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既关注道路本身,也关注道路所经过的沿线区域,还要进一步关注道路上的人与文化的流动与变迁,层层递进、深入,推进青海道的研究体系不断立体化、多元化。
第二,开辟族群与道路结合研究的新思路。一条道路的畅通离不开人群的绾毂,而汉唐时期青海道沿线民族众多、文化面貌复杂,沿途考古发现的文物材料是否能简单对应某一民族,即考古学文化是否可直接与某一族群画上等号,这是需要审视和研究的。随着族属和族群等概念和理论的介入,考古学研究中族属的复杂性远非考古学文化所能涵盖。特别是不同族群杂处而产生的文化碰撞与融合,对考古学文化提出的挑战超乎寻常。以都兰墓群族属研究为例,“希望赋予特定器物或纪念物某种身份,一直是考古学探究的核心,而这种身份经常是用族群或者创造它们的‘人群’来表示”[135]。但是代表某特定群体认同的文化象征,会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发生转变[136],且族群并非是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群体,而是在文化差异基础上建构的群体[137],显然族属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族属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其对所处政权的认可等关系密切。
同时有些人群为保护族属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因势而改变其政治认同,从而会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族属的血缘、地域和文化之间的纽带。对于这种多元文化的墓葬,我们必须考虑特定形制分布与来自某特定背景的物质文化整个组合的关系,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它们[138]。此时丧葬制度作为一个族群对其族属认同的最核心表达,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与主观认同往往蕴藏其中,对丧葬制度的综合考察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判断墓葬主人族属的突破口之一。
第三,将文化变迁考察与道路变迁研究有机融合。美国学者班茂燊(Marc S. Abramson)曾提出族群变迁的模式有三大趋势:一是“绅士化”;二是“军事化”;三是“本地化汉化”。其中“本地化汉化”最常见却最不被重视[139]。以青海道研究为例,羌、吐谷浑、吐蕃、粟特等民族因各种方式产生了民族文化的变迁,与此同时青海道的路网勾连也在不同情境下发生细节变化,这也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
纵观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青海道上所活跃的主要民族与沿线途经区域均较为固定。道路本身长期受吐谷浑、吐蕃控制,处于西北边陲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对峙地带,军事化意味十足。因此对于青海道的切片式观察,无疑对整个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一斑窥豹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青海道研究,特别是青海道所反映的文化变迁研究理路和相关方法论,无疑应具有更普遍的价值和意义。
[1] 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2):42-46。
[2] 张得祖:《古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青海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5):56-59。
[3] 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刊》1947(5):111-146。
[4] [日]松田壽男:《吐谷渾遣使考》,收入《松田壽男著作集·東西文化の交流Ⅱ》,東京:六興出版,1987:68-126;薄小莹:《吐谷浑之路》,《北京大学学报》1988(4):70-74。
[5]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 周伟洲:《丝绸之路的另一支线——青海道》,《西北历史资料》1985(1):11-26;赵荣:《青海古道探微》,《西北史地》1985(4):56-61;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历史地理》1986(4):145-151;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2005(2):94-98。
[7] 周伟洲:《古青海路》,《西北大学学报)》1982(1):65-72。
[8] 臧振:《“玉石之路”初探》,《人文杂志》1994(2):79-89。
[9] 刘学堂:《史前彩陶之路:“中国文化西来说”之终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21(5)。
[10] 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2):79-88。
[11] 牛钧鹏、李健胜:《回顾、反思与展望——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1):11-20.
[12] 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1995(1):291-334,收入氏著:《丝绸之路考古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8-95。
[13]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48:6-7。
[14]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1948:1-55。
[15]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97-584,701-754。
[16]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1):105-110。
[17] 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2017:8-95。
[18] 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1):65-72。
[19] 赵荣:《青海古道探微》,《西北史地》1985(4):56-61。
[20] 薄小莹:《吐谷浑之路》,《北京大学学报》1988(4):70-74。
[21] [日]前田正名:《西夏時代における河西を避ける交通路》,《史林》第42卷,1959(1):79-103;[日]阿子島功:《青海シルクロードの自然環境——谷あいの道、水草の道、緑洲の道、冰原の道》,《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中国·青海省におけるシルクロードの研究)第14卷,2002(1):37-77;[日]铃木隆一著,钟美珠译:《吐谷浑与吐蕃之河西九曲》,《民族译丛》1985(3):47-51;[日]山口瑞鳯:《白蘭とSum-paのrLangs氏》,《東洋學报》第52卷,1969(1):1-61;等等。
[22] [日]佐藤长著,梁今知摘译:《隋炀帝征讨吐谷浑的路线》,《青海社会科学》1982(1):90-95。
[23] [日]佐藤长:《チベット历史地理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8:123-124。
[24] 陈良伟:《松灌丝道沿线的考古调查 ——丝绸之路河南道的一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6):62-7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松潘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松潘县松林坡唐代墓葬的清理》,《考古》1998(1):65-7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丝绸之路河南道沿线的重要城址》,《考古学集刊》第13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38-268。
[25]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2002:1。
[26]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2002:序言第3页。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丝绸之路河南道沿线的重要城址》,《考古学集刊》第13集,2000:238-268。
[28]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2002:13。
[29] 李健胜、董波:《刻写青海道》,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11。
[30] Tong Tao, The Silk roads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from the Han to Tang Dynasty): as reconstructed from archaeological and written sources, Oxfor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2013.
[31] [日]松田壽男著,周伟洲译:《吐谷浑遣使考(上)》,《西北史地》1981(2):81-94;[日]松田壽男:《吐谷渾遣使考》,收入《松田壽男著作集·東西文化の交流Ⅱ》,1987:68-126。
[32] 周伟洲:《吐谷浑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1-54。
[33] 周松:《吐谷浑遣使东魏路线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3):19-28;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2002:252-302;李健胜、董波:《刻写青海道》,2017:167-195。
[34] 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35] 毕艳君、崔永红:《古道驿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
[36] 周伟洲:《吐谷浑史》,2006:135-136。
[37] 张得祖:《古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青海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5):56-59。
[38] 苏海洋、雍际春:《丝绸之路青海段交通线综考》,《丝绸之路》2009(6):39-42。
[39] 崔永红:《丝绸之路青海道盛衰变迁述略》,《青海社会科学》2016(1)9-16;崔永红:《丝绸之路青海道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绪论。
[40] 李健胜、董波:《刻写青海道》,2017:121-136。
[41] [瑞典]斯文·赫定著,周山译:《亚洲腹地旅行记》,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42] Wilhelm Filchner, Bismillah! Vom Huang-Ho zum Indus, Leipzig: F.A. Brockhaus, 1938: 102-103.
[43] 安志敏:《青海的古代文化》,《考古》1959(7):375-383。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丝绸之路河南道沿线的重要城址》,《考古学集刊》第13集,2000:238-268。
[45] 许新国:《青海省考古五十年述要》,载氏著:《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25。
[46] 相关墓葬资料可参考发掘简报、报告及赵生琛等:《青海古代文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104-114;国家文物局主编、青海省文化厅编制:《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42-48。
[47] 相关墓葬资料可参考发掘简报、报告,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8):19-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2021(8):45-72;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青海都兰哇沿水库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辛峰主编:《海西州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精选》,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3:112-157。
[48] 许新国:《青海考古的回顾与展望》,《考古》2002(12):3-11,97-98;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2005;徐承炎、夏吾卡先:《青海吐蕃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西藏研究》 2019(1):54-63;青海省博物馆编著:《尘封千年的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49] 赵深琛:《青海西宁发现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通讯》1958(1):64-65。
[50] 袁曙光:《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2(2):67-71;雷玉华、李裕群、罗进勇:《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7(6):84-93,96-97。
[51] 冯汉骥:《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全国基建出土文物展览会西南区展览品之一》,《文物参考资料》1954(9):110-120;刘志远、刘廷璧编:《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袁曙光:《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代石刻造像》,《四川文物》1991(3):27-32;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10):19-38。
[52] 张肖马、雷玉华:《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10):4-18。
[53]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11):4-20,97-100。
[54] 成都考古研究院编著:《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55] 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8):436-440。
[56] 李琴:《探寻吐谷浑伏俟城》,《大众考古》2021(5):63-70。
[57] 李国华:《吐谷浑遗存的初步探索》,《北方民族考古》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201-221。
[58]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1):105-110。
[59] 王瑄:《汉唐之际“青海道”墓葬概论——以都兰吐蕃墓葬为中心》,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60] 肖永明:《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青海民族研究》2008(3):57-63。
[61] 阿顿·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中国藏学》2012(4):117-136;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豺)纪年〉残卷的研究》,《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95-108;程起骏、毛文炳:《倾听千座古墓的诉说——就都兰古墓群的文化归属与许新国先生再商榷》,《中国土族》2006(3):9-12;仝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2012(4):467-488;许新国:《青海省考古工作五十述要》,载氏著:《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2006:16-18;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89;霍巍:《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3):24-31。
[62] 参见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63、124-126、142-144;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史学集刊》2013(6):3-24;仝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2012(4):467-488、547-550。
[63] 韩建华:《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吐蕃化因素分析》,《考古》2022(10):100-109。
[64] 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藏学学刊》第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65-170;肖永明:《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青海民族研究》2008(3):57-63;仝涛:《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18(6):94-104。
[65] 孙杰:《青海海西地区5-8世纪墓葬文化因素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66] 许新国、赵丰:《都兰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15,16,收入氏著:《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2006:176-198。
[67]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1):3-26。
[68] 许新国:《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中国藏学》1997(3):67-82。
[69] 许新国:《都兰出土织锦──“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青海社会科学》2007(2):73-76。
[70] 许新国:《都兰出土大批唐代丝绸见证丝绸之路青海路》,《文物天地》2004(10):3;许新国:《吐蕃墓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藏学学刊》第3辑,2007:93-116。
[71] 赵丰、齐东方主编:《锦上胡风——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4-8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72] 赵丰:《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合肥:黄山书社,2016。
[73]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纺织品珍宝》,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
[74] [瑞士]阿米·海勒著,霍川译:《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3):32-37;Amy Heller, "Tibetan In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efact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1, 2013: 259-291.
[75] 霍巍:《金银器上的吐蕃宝马与骑士形象》,《西藏大学学报》2014(1):77-82;霍巍:《吐蕃金银器中的带翼神兽》,《中国西藏》2018(1):72-75;霍巍:《考古图像中的吐蕃胡瓶》,《中国西藏》2016(4):82-85。
[76] 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考古学报》2009(1):89-128、159-164。
[77]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动物形银器》,《中国西藏》2003(1):66-72;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4):31-45。
[78] 李璟:《吐蕃金银器纹样图像考》,西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79] 朱建军:《交融与互鉴——新见吐蕃、吐谷浑出土文物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
[80] 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1):56-69;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西藏研究》2007(2):49-61。
[81] 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中国国家地理》2006(3):92-93;罗世平:《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3):94-95;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3):96-98。
[82] 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艺术史研究》第九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257-276。
[83] 霍巍:《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敦煌学辑刊》2007(1):82-94。
[84] 仝涛:《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所见丧礼图考释》,《考古》2012(11):76-88。
[85] 曹中俊:《粟特艺术东传与丝绸之路青海道——以彩绘棺板画为考察核心》,《丝绸之路考古》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121-143。
[86] 宋耀春:《青海郭里木出土棺板画数据统计与分析》,《藏学学刊》第9辑,2013:58-69。
[87] 辛峰、马冬:《青海乌兰茶卡棺板画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7(3):1-9。
[88] 孙杰、索南吉、高斐:《青海海西新发现彩绘木棺板画初步观察与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80-290。
[89] 张建林、才洛太:《青海藏医院博物馆藏彩绘棺板》,Shing Müller, Thomas O. Höllmann, and Sonja Filip, Early Medieval North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Evidence,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Wiesbaden, 2019: 261-282.
[90] [日]岚瑞徵:《六朝時佛僧的往來的西域交通路線及其記錄》,《佛教學論叢》1936(1):22-33。
[91]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1):105-112。
[92] 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1979:1-20,收入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104-117。
[93]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2002:303-313。
[94] 郭盛:《青海“河南道”佛教传播源流考释》,《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1):91-99;曹中俊、李顺庆:《经丝绸之路河南道至建康僧人弘法事迹考》,《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24-238。
[95] 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11):40-50。
[96] [日]山名伸生:《吐谷浑と成都の佛像》,《仏教艺术》218,1995:11-38。
[97] [日]吉村怜:《成都万佛寺址出土佛像と建康佛教:梁中大通元年銘のインド式佛像について》,《仏教艺术》240,1998:33-52;收入吉村怜著,卞立强等译:《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17-234。
[98] 孙杰:《佛教初传“湟中”研究——以“湟中”画像砖墓出土佛教图像为例》,《佛学研究》2019(1):295-306。
[99] 仝涛:《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中山大学学报》2019(5):140-151。
[100] 王育成:《都兰三号墓织物墨书道符初释》,收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35-142。
[101] 张泽洪、焦丽锋:《丝绸之路河南道多元宗教文化传播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5(6):41-49。
[102] 许新国:《都兰热水血渭吐蕃大墓殉马坑出土舍利容器推定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1):95-109。
[103] [瑞士]阿米·海勒著,霍川译:《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3):34。
[104] 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2005(2):94-98。
[105] 张建林、才洛太:《青海藏医院博物馆藏彩绘棺板》,Shing Müller, Thomas O. Höllmann, and Sonja Filip, Early Medieval North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Evidence,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Wiesbaden, 2019: 261-282.
[106] Andreas Gruschke, The cultural monuments of Tibet's outer provinces: Amdo, vol.1, The Qinghai part of Amdo, 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2001: 105-110.
[10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热水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108]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09] 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
[110] 赵丰主编:《西海长云:6-8世纪的丝绸之路青海道》,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
[111] 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2):42-46。
[112] 吴焯:《古代青海交通西域的路线及其历史沿革》,《西域研究》1992(2):24-33。
[113] 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刊》1947(5):111-146;收入氏著:《西域史地考古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53-493。
[114] 周伟洲:《吐谷浑史》,2006:132-141。
[115] 罗新:《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1):43-52。
[116] 李朝:《丝路青海道及其文化》,收入《柴达木历史与文化》编委会编:《柴达木历史与文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87-139。
[117] 李朝:《吐谷浑与丝绸之路》,《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2):33-39。
[118] 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14-131。
[119] 许新国:《都兰出土蜀锦与吐谷浑之路》,载氏著:《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2006:199-212。
[120] 朱悦梅、康维:《吐谷浑政权交通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121] 仝涛:《考古发现填补青藏高原丝路缺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25日,第7版;霍巍:《“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社会科学家》2017(11):19-24;霍川、霍巍:《汉晋时期藏西“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历史意义》,《西藏大学学报》2017(1):52-57;余小洪:《“高原丝绸之路”路网结构的考古学构建与文化内涵》,《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2019(2):21-27。
[122] 沈琛:《麝香之路:7—10世纪吐蕃与中亚的商贸往来》,《中国藏学》2020(1):49-59。
[123] 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194-195。
[124] 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79(1):1-20;收入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1986:104-117。
[125] 周松:《柔然与南朝关系探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0(2):44-50。
[126]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2002:252-300。
[127] 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1983:194-195。
[128]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42-49。
[129] [法]魏义天著,王睿译:《粟特商人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90-92。
[130] 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9):49-54。
[131] 主要研究成果见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2006。
[132] 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2005(2):94-98。
[133] 李瑞哲:《粟特人在西南地区的活动追踪》,《西部考古》第1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295。
[134] 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前言。
[135] [英]希安·琼斯著,陈淳、沈辛成译:《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9。
[136] C. F. Keyes,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Ethnic Change, ed. C. F. Key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14-15.
[137]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主编,李丽琴译,马成俊校:《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23-26,37。
[138] [英]希安·琼斯著,陈淳、沈辛成译:《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2017:170。
来源:原文引自曹中俊《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回顾与展望》,《藏学学刊》第27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2年在线股票配资门户网,78-96页。
发布于:陕西省富华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